姜育恒的歌曲(姜育恒的歌曲专辑)
诗
青·年·诗·人
诗人简介
郁颜,本名钟根清,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于浙西南一个叫“玉岩”的小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诗刊社第29届“青春诗会”。现居浙江丽水,供职于丽水日报社。
代 表 作
身体里的故乡
身体有它的过错、隐秘与局促
每一处伤疤,都是它的故乡
它们替你喊疼,替你埋葬悔恨
隐瞒你,包容你,忍耐你,又无声地陪伴你
星夜感怀
躺在草地上,星星盯着我的眼睛,这多么让人着迷
风一吹,我的心就动了,这多么让人沉醉
我的身体,是今晚狭长的夜空
有时星星遮住我,有时我遮住星星
血脉在体内醉生梦死,运送多余的时间
除了衰老,已没什么值得去抵抗
马铃薯记
那年,我小心翼翼地
把马铃薯一个个藏进挖好的土坑里
母亲在边上撒上一掊草木灰
父亲呢,一一给它们浇上了粪水
暖风吹干脸颊上的汗液时
我们便往马铃薯们身上
盖上土,像是一场埋葬的仪式
我们默默地弯曲着腰
二月的乡野
多了一群忍住光芒的星子
为了再次和我们见面,才几天工夫
它们就狠狠地破土,并吐出了绿色的嫩芽
闪电一般,比呼吸还迷人
省 略
如果可以,我多想
省略来时的线索和逃离的方向
省略一生的情节和高潮
省略身边的色彩、气味、词语和声音
也省略多余的抒情和叙述
省略猝不及防的青春、流年和时光
当我一个人站在河面之上,可以
很轻很轻地,告诉你们——
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请省略我
像省略,彼岸那些记忆和花草一样
瓯 江
有一次,我一个人
站在桃山大桥上
看河岸边小小的洼地四周
长满了很多芦苇
风来时,他们相互挨紧
风走后,一旁困倦的瓯江
像芦花盛开一样
有种无法形容的宁静
除了看不见的流水声,除了我目力所及的
茫茫夜色
当我像一只飞离树枝的鸟一样
走过大桥时,身后的瓯江
有如寂静,恋恋不舍地
向着我蔓延过来
哗哗——哗哗——哗哗

人间草木
亲近草木,被它们深深吸引
深爱它们,却从不说出口
在南方小城的白云森林公园里
它们有着温暖的脸庞和气息
落地生根,它们在人间找准了位置
并知晓土地下的秘密
它们淡薄的心,尘埃一样沉默、朴素又卑微
忠于泥土,漫山遍野地生儿育女
它们不离不弃,不事张扬
面对风雨,逆来顺受,从不向任何人道及
它们的欢欣,就是在夕光中侧身低语
长满皱纹
在秋风中,当它们一次次挨近我
我忽然觉得,在尘世还一次次地被爱着
这让我,加深了对它们的热爱
包括爱它们所热爱的
新 作
归来者(组诗)
■郁 颜
致友人
与时间对抗、共存
与过去的自己
重逢、相认
再被此生无边无际地流放
省己书
对这个世界
所知还是甚少
总是沉湎于记忆
试图接通另外一个我
面对生活,常无言以对
而命运,总是不可言说
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
差点就忍不住,要把自己和盘托出
清 晨
清晨点亮了露珠的眼睛
风自耳边吹过,像打开了两扇窗户
刚下过雨的泥地里,蚯蚓在松土
枝头的鸟儿,抖着羽翅,在练习歌唱
此刻,我几乎是多余的
泥人歌
让飞鸟归于苍穹
山川归于沧海
万物各得其所
以前是肉体
现在是骨头做的灰
到最后都要埋于地下
他一生都囚禁在泥土里
上 苍
苍天在上面
我在下面
花朵在上面
土在下面
有些土,在我上面
有些土,在我下面
山中一日
友人一早就上了白云山
在白云寺
吃斋饭、喝素茶
真是叫人羡慕
他活成了一朵白云
在山之巅,俯瞰着众生
归来者
根在地底下用力逃窜
像水困于河,时间困于钟表
我在地上迎风奔跑,也曾是个忧郁的少年郎
异乡记
我是我的囚徒
有软弱的皮囊和坚硬的骨头
我是我的反动派
和一切苦痛的源头
我是一个卑贱者
和命运的执行者
我悲伤,是为了
获得喜悦的意义
我写作,以对抗虚无
以忘却生活给我的一次又一次羞辱
我是我的异乡
生下来,就是为了找寻归途
隧 道
光圈夹杂着尘土
有如一段隧道
穿过我
落叶纷纷扬扬
这一次远眺,因为虚无的加入
而多了几分仪式感
停留于此
我有一半是肉做的
有一半来自黑暗的记忆
阴 谋
身体里
关着暴君、小丑和盗贼
这一生,总是活在压抑中
为了不放它们出来
身体里一定
还藏着很多阴谋
会时不时,来一次临时起意
漫不经心的时候
会惹怒它、怠慢它
最让人痛恨的是
永远不知道
下一次,它会以怎样的疼,提醒着——
你还在
醒世录
不能再轻易谈论人生了
它的有用和无用都不是我的事
那些偏袒、包庇,甚而纵容
值得一次又一次忏悔
可还是弄不明白
疼和痛的界限,命和运的暧昧不清
发 狠
这些年,被人爱过
也爱过一些人
挥霍过时光
也享用过它的恩泽
对不起,这三十多年来
我仍然是一个自私的人,很少掏心掏肺
编织过很多借口,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从来没有对自己发过狠
唯有伤心时
才记起,要狠狠抽自己一巴掌
【自我诗歌观点】
对抗虚无的悟道之旅
郁颜
在浙西南的山旮旯里,有一个小镇,小镇的名字秀气又拙朴——玉岩。
约莫是初中毕业时,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郁颜,和那个生我养我的小镇有着同样的读音。
很多年后,“生于浙西南一个叫‘玉岩’的小镇”,在我的创作简介里都是无法省去的。
我是从2004年上大学时开始写诗的。
高考失利,上不了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学校,上的是本市一所地方院校,离老家玉岩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在当时,可谓是异常失落。在入学不久的一个周末,百无聊赖的我,加入了文学社团——露路诗社。这仿佛是我和诗歌的一种巧遇,而因内敛的性格使然,这似乎又是一种必然。
那真是一段骚动而又充满激情的青春期写诗时光!上课写,下课写,大半夜还写。多的一天,甚至可以写上十多首。和很多同年代的大学生诗人一样,那时也深受北岛、海子、顾城等诗人的影响。诗歌写得朦朦胧胧,有的连自己也看不懂。那时的学业,自然是被搁置在一边了。好在大学,还算是包容的。写诗、发表、获奖、编诗、搞活动,玩得是不亦乐乎。
“纯情的姿态、华美的言辞,平缓中略带几分忧伤的语调,他是那样沉溺于自己制造的语言游戏中……到底是仅仅学会了这一招,还是阶段性的个人偏好?这个问题,就不是我能说得上来了,还是让他在今后的作品中自己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吧。”大学期间,诗人柯平在给我写的一篇评论里这样写道。他给了我写作最初的鼓励和期待。
2007年10月,也就是大四上学期,我在《星星》诗刊首次发表了习作。2008年3月,在大学临近毕业时,又非常意外地获得了《星星》诗刊颁发的全国年度大学生诗人奖,为大学的写诗生涯画上了一个也算圆满的句号。当时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对心灵的关注和探求,使郁颜的诗具有一种沉思冥想的美。他善于以轻灵的语言勾勒出好幻的情景,而包裹其中的是诗人沉甸甸的内心。”
2008年7月,我大学毕业,留在当地一家报社做了一名新闻记者,工作、生存的压力,让我无暇顾及诗歌写作。在社会现实与诗歌理想之间错位、游移、徘徊,诗歌“产量”急剧下降。
告别了青春年少的莽撞,开始自觉写作后,我也在有意地找寻更加个人化、更加自我的表达方式。
我工作、生活的小城丽水,有条母亲河,名叫瓯江。每当我身心疲惫时,总喜欢到江边走走,吹吹风、发发呆。水面的涟漪、两岸的芦苇,给了我辽阔而流淌的诗意享受。我开始静下心来,专注于对一条江的抒写。2009年7月,我第一次如愿以偿地在《诗刊》发表《冷暖自知》(组诗5首)。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偏居于浙西南一隅的我,从写瓯江,到写一草一木,再到写山水,完成了与自然的一次次对话。漫步山野,亲近草木,让我获得了一份宁静的力量。
我承认,我是个胸无大志之人。然而,什么又是大志呢?
山水让我沉醉,让我敬畏,让我懂得慈悲。同时,也给我以朴素的情怀,和无限的诗意——这,何尝不是一种相遇?
在写好“人”这首更大的“诗”的过程中,我甚至梦想学古人——“植松柏”“筑木屋”“打铁”“做木”“翻阅线装书”“着长衫”“捋须吟咏”“醉卧山水间”……跟随他们观天象,与他们谈理想。
古人生活里的山水,让人心向往之——在山水间,无论是枯坐,还是打坐,都适合抒情、怀古。
诗人叶延滨说:“写山水诗使郁颜得到了诗坛的认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同时又找到了自己一些新的可能的发展空间。”
诗人梁平说:“郁颜的诗不随波逐流,不故弄玄虚,写得结实而富于想象。他笔下的山水、草木与人世,可以听见呼吸和血脉的流动,皆有冷暖。因而,在他的诗里,无论悟道、修身还是养性,我们能够读到一种朴素、一种开阔。可以说,在80后诗人群体写作中,郁颜无疑有极高的辨析度。”
2013年,我以一组山水诗参加了诗刊社第29届“青春诗会”,用老诗评家谢冕的话说,就是“正式向诗坛报到”。
从习诗到向诗坛报到,我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这十年,不短也不长。在很多人眼里,我可能还是个幸运儿。
如今,回头一看,其实是应该值得警惕的。我不愿就此,被贴上“山水诗人”这样的标签。那些情真意切之时写就的所谓山水诗,又是如此的虚弱和不真实。
诗人、诗评家霍俊明在一篇评论文章里说:“郁颜沉浸于‘新山水诗’的写作冲动和欢欣之中。他的那些诗有灵气,有想法,当然对于他的山水诗我也有过不小的疑虑。如何在一个灰霾滚滚的时代写作那些看起来已是恍如隔世的‘自然’诗篇?”
我们这个时代,正被崛地而起的高楼,冰冷的机器,一种失去温度的节奏所充斥。将自然的“根”,连根拔起。当我们再次走进山水,这个山水已经不是以前的山水了。
这些年来,我生活的这座南方小城,也加快了它的城市化进程。故乡、故土,正在时刻萎缩。这个过程,也曾让我感到恍惚、惶恐与失落。
我们终要妥协、隐忍,或者自欺欺人。
告别纯粹的山水诗写作,这两年来,我的写作沉陷在对于个体的“我”的确认——怀疑——确认之中,期间还夹杂着对命、命运的一些体验和诘问。
在《异乡记》里,我这样写道:“我是我的反动派/和一切苦痛的源头//我是一个卑贱者/和命运的执行者/我悲伤,是为了/获得喜悦的意义//我写作,以对抗虚无/以忘却生活给我的一次又一次羞辱。”
我在《诗刊》2016年2月上半月“每月诗星”栏目刊发的《身体里的故乡》(组诗)里这样写道:“身体有它的过错、隐秘与局促/每一处伤疤,都是它的故乡//它们替你喊疼,替你埋葬悔恨/隐瞒你,包容你,忍耐你,又无声地陪伴你。”
这组诗被评论家赵思运认为是“转型之作”,并被看作是“从文化标本的描摹到生命体验的掘进”。他说:“当初郁颜在痛苦中‘怀着对山水的热爱,写下了这些不合时宜的所谓的山水诗’,而今将会在山水诗与现实世界的两极张力中,将更加复杂的人性生存面貌与生命体验的分裂感充分表达出来。”
诚如斯言。
写诗,就是一场对抗虚无的悟道之旅。
唯愿在今后的创作中,能打开更多幽闭的意境和诗思,重新回到当下日常,在现实与幻境的不断错位、纠结与抽离中,打开身体与记忆之门,刷新惯有的认知与体验,写作出更多无愧于心的生命之诗。
【评论】
从文化标本的描摹到生命体验的掘进
——读郁颜组诗《身体里的故乡》
文/赵思运
基于两年前郁颜诗集《山水诗》留下的深刻印象,我曾把他称为“逃往山水理想国的‘移民’”。郁颜在自序《山水之心》里写道:“为天地立不了心,那就胸怀一颗山水之心。以此,复活朴素的情怀,获取宁静的力量。”所以,他写道:“我是多么崇尚古人的活法/一袭青衫/蓄发、捋须/山中捡拾枯木,生火、煮酒”(《山中拾遗》)。这种活法固然十分动人,乃至诱人,但是,我们需要警惕将“回归传统诗学”做单向度的理解,因为现在的诗学探索已经进入一个多维度多方位的综合阶段。“回头看”只是一种维度,而不是一种诗学方向。对于一个有诗学野心的诗人来说,他还需要建构起更加宏阔的视野。这两年,郁颜在努力寻求新的突破,试图从山水诗的文化标本范式转型为现实抒写范式,触摸人世温情,注重身体(生命)的在场。《身体里的故乡》即是郁颜创作转型之作。他做出的积极调适,值得我们关注。
郁颜的《山水诗》以独语体的抒情语式为我们营造出一个与世隔绝的自足世界,他的精神存在是独处而不是群居。而在《身体里的故乡》这组诗里,他打破了幽清、幽静、幽闭的意境和诗思,从山水的文化标本里走出来,充盈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重新回到日常和现实,赋予了诗歌文本一种纯棉质地。“亲手做一顿早餐/一个人安静地吃完//打开窗帘,坐在沙发上发一会儿呆/和身体里的每一个旧我打个招呼//和春天里的每一个面孔/一一相认//匆匆韶光,允许自己做件傻事/学羊叫、学马叫、学风叫”(《这人世的草原细雨绵绵》),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安宁妥帖的灵魂区。诗人还自拟为一棵“树”,以第一人称传递出大自然与人的亲密关系:“我长得不会那么快/你还来得及//凑上来环抱,还可以在我身后十指相扣/春天来了,也可以围坐在我身边一起聚聚餐/吃吃喝喝,有说有笑/一阵风吹来,摇响满树的叶子/我也会忍不住发出声音”(《树》),人性的春风就这样温暖地吹拂着读者的心田,令人回味咀嚼。《一辈子一定要去做很多无意义的事》里一口气儿用20个“比如”铺陈了20个蒙太奇镜头,在简洁而丰富的日常情境里,试图寻找生活的真意:“比如写一首诗/把无意义写得有意义/再读成无意义/比如把六个句号连成一个省略号”。“一辈子一定要去做很多无意义的事”其实就是一个反语,它表达的是生活的意义往往在于“无用之用”,在于“无意义的意义”。这首诗让我们想起姜育恒的歌曲《再回首》里唱的“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禅意弥满,真意充盈。
郁颜走出山水诗的幽闭,还有一个鲜明的表现,就是从山水诗的静态型诗意嬗变为动态型诗思。在他的《嚼雪的马》《丢》《行李》《故人帖》《京杭大运河》等诗作中经常出现“异乡的冬夜”“走在路上”“远方”“歧途”“行李”“晚归的故人”“异乡人”等意象。这些意象不再是“小桥流水人家、枯藤老树昏鸦,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古典游子行吟,而是具有了现代人“在路上”的灵魂漂泊的喟叹。《嚼雪的马》和《故人帖》就像两幅幅剪影——前者以羁旅行役之马,后者以“晚归的故人”——状写途中游子,二者都以雪地为背景来烘托异乡人的冷寂与孤独,情透纸背,力透纸背。《丢》接续传统文学中“在路上”的母题,但是诗思向度是现代的;不是“回头”式,而是前行式的寻找。在“走丢”与“寻找”的瞻前顾后中,暗示出来的是关于“自我寻找”的现代哲思。《行李》和《京杭大运河》所折射的人生履历则更为丰富,已经完全从山水诗的文化体验范式转型为人生体验范式。“他是大地母亲怀里一个破旧的行李/装满了疲倦、愧疚/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仇恨、不解、揪心的疼/还有软弱的宽容”(《行李》),这是一首用“沙哑的喉咙”哼唱的“沧桑的歌”,其中饱含了多少人生况味,“滚滚长江东逝水”又蕴藉着多少人生的汗水与血泪!《京杭大运河》则试图在历史维度上拓展出新境。那“光滑的青石板”“墓碑”“尸体”“浑浊的运河水”“残缺的欢宴”等历史意象,所渗透的个人的命运感与家国情怀,都加深了历史容量和厚度。
郁颜无论倾心于返古,还是“在路上”的向外开拓,都离不开他的“故乡情结”。其笔名“郁颜”乃出生地“玉岩”之谐音。他在每次的作者介绍里都会出现“生于浙西南一个叫‘玉岩’的小镇,现居丽水”。他的曾经的“山水诗”是从他的故乡“丽水”和“瓯江”里孕育出来的。“丽水”“瓯江”“玉岩”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和物理位置,更是一种灵魂寄居地的象征,已经充分地浸染了郁颜的灵魂色泽。因此,他的“故乡情结”带有强烈的“身体/生命”印迹。“故乡”强烈的的身体(生命)在场性使得他的诗思具有了鲜明的内倾特质,就像那首《身体里的故乡》:
身体有它的过错、隐秘与局促
每一处伤疤,都是它的故乡
它们替你喊疼,替你埋葬悔恨
隐瞒你,包容你,忍耐你,又无声地陪伴你
郁颜的诗思在向外拓展与内倾性之间,形成了较大的张力。他的灵魂的触角一方面向历史空间延展,另一方面,灵魂的眼睛又向生命的内在腠理凝视。《打坐颂》即是典型的内倾式抒情:在漫漫时光里,诗人俯首打坐,直到“坐进肉里、骨里、心里、土里”,“细雨绵绵/这潮湿的出土文物/坐进了荡漾而漫长的死生里”。从诗艺上讲,《指甲帖》尤其可圈可点:
它们跟随我这么多年
年岁渐长,指甲里的月亮
有的已经藏进了肉里
有的还固执地亮着,对抗着体内的黑暗
小诗在“指甲上的半月痕”与现实中的“月亮”之间产生联想,自然物象与生命体征之间构成了隐喻关系,将月亮辐射出的生命之光与生命磨蚀带来的“黑暗”对比,构思奇特,深化并锐化了生命体验。
两年前,郁颜吟咏着“翻阅线装书。以清澈的山泉为明镜/洗濯疲惫的身躯,与涟漪里/另一个褶皱的我相遇”(《相遇》),带有自我确证的意义。然而,正如郁颜在《山水诗》的自序《山水之心》里所说,“当我们再次走进山水,这个山水已经不是以前的山水了。我们终要妥协,要隐忍,要自欺欺人。”恶劣的现实生态对于山水的挤压,迫使深深浸润于传统山水文化的现代人不得不抽身而返,扎根于严峻的现实生存语境。当初郁颜在痛苦中“怀着对山水的热爱,写下了这些不合时宜的所谓的‘山水诗’”,而今将会在山水诗与现实世界的两极张力中,将更加复杂的人性生存面貌与生命体验的分裂感充分表达出来。
中国传统山水文化,作为一种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的价值表征,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不能把它简化为一种诗学态度,更不是一种道德态度。否则就有可能陷于文化保守主义。如果说,郁颜的《山水诗》代表了一种文化寓言的象征意义,那么,组诗《身体里的故乡》则意味着郁颜尝试着开启了将文化态度转化为现代生命体验的生态诗学实践。
<< 上一篇
下一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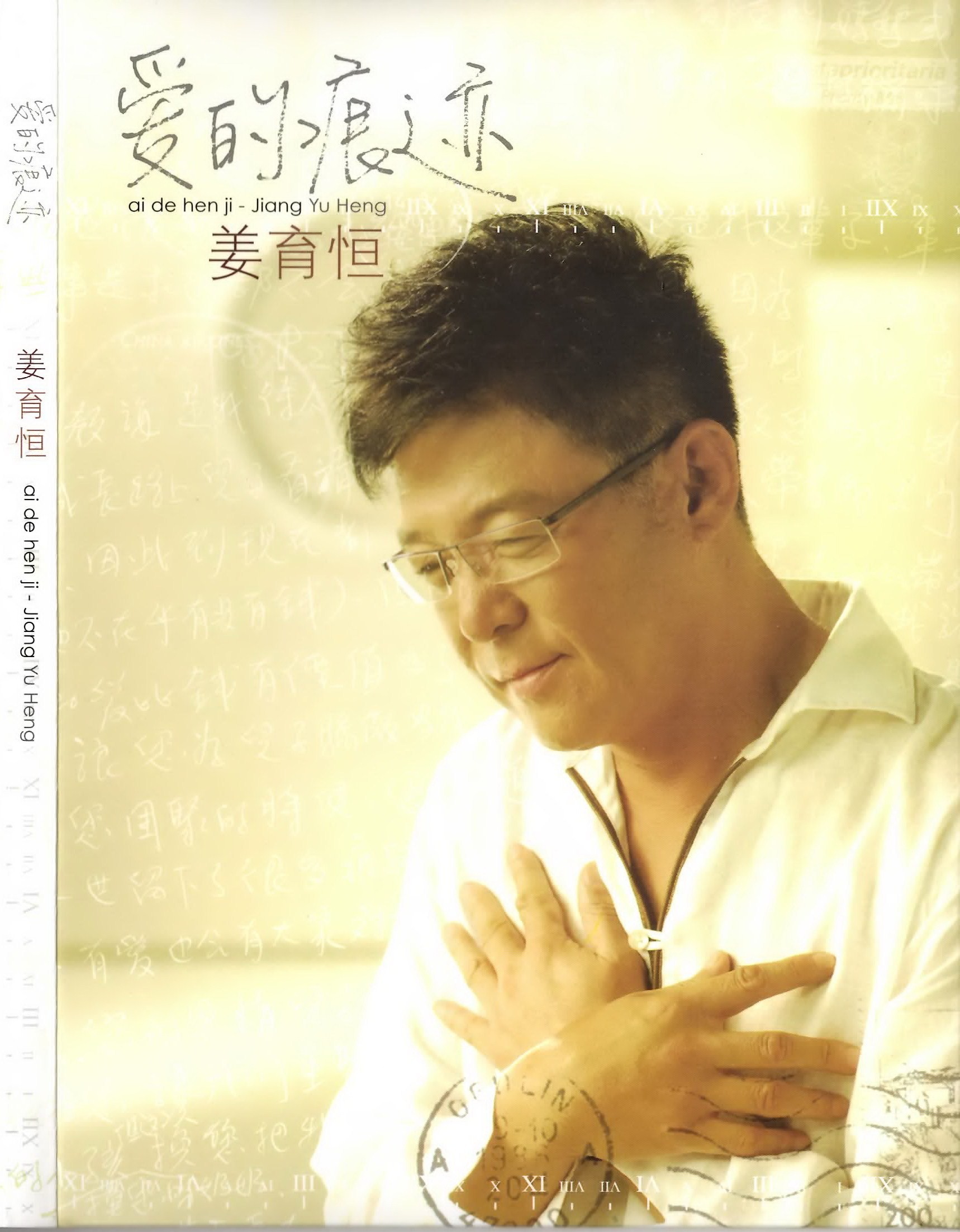
网友留言(0 条)